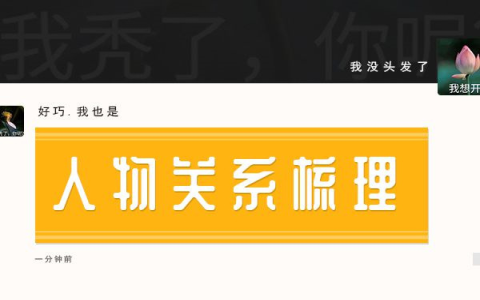從讀到第一頁(yè)杜拉斯時(shí),他便無可自拔地愛上了她。準(zhǔn)確說是她的文字。通信六年,終于得見,從那一天起,他便成為她的情人、演員、助理、司機(jī)、護(hù)工,哪怕對(duì)方大了自己整整38歲。此后16年,揚(yáng)·安德烈亞,這位連名字也由杜拉斯改定的年輕人,始終陪伴杜拉斯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,成為她豐富情史的最后一筆。
你以為這是一對(duì)神仙眷侶?可殊不知,這份愛狂熱到近乎窒息,甚至有著情感控制和暴力的傾向。而又是為什么,這位年輕情人在短暫逃離后,仍選擇回到杜拉斯的身邊,甚至在去世后仍選擇與之合葬?亮相上海國(guó)際電影節(jié)展映“從文學(xué)到電影:瑪格麗特·杜拉斯誕辰110周年”的影片《我想聊聊杜拉斯》,帶我們回到了二人故事的最開始……
電影依據(jù)1982年揚(yáng)·安德列亞接受記者米歇爾·芒索采訪的錄音整理而來。彼時(shí),這位比杜拉斯小38歲的情人,已經(jīng)與她同居兩年。面對(duì)杜拉斯的鄰居閨蜜、知名記者,揚(yáng)巨細(xì)靡遺地傾訴著自己從粉絲到情人的身份變化以及心路歷程,以自己的視角定義詮釋這段驚世駭俗的忘年戀,袒露自己對(duì)杜拉斯的愛慕與欣賞,也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地流露著對(duì)方完全支配自己生活的恐懼與無奈。
電影的特別之處,在于其95%的情節(jié),只發(fā)生于逼仄的閣樓房間,只有揚(yáng)的自陳。而談話電影能牢牢抓住觀眾的首要原因,當(dāng)然就是這段經(jīng)歷的特殊:從揚(yáng)22歲時(shí)閱讀到《塔爾奎尼亞的小馬》起始。這一讀,便令讀哲學(xué)的揚(yáng)一往情深。此后杜拉斯執(zhí)導(dǎo)的《印度之歌》來到揚(yáng)所在的小城舉辦觀影見面會(huì),揚(yáng)要到了杜拉斯的住址,并開啟長(zhǎng)達(dá)六年的通信。直至有一天,揚(yáng)通過杜拉斯的真名在黃頁(yè)上找到她的電話。沒多久杜拉斯便提議見面。而這一見,他便沒能再離開她。時(shí)年揚(yáng)28歲,杜拉斯66歲。
影片全程幾乎以口述展開,透過揚(yáng)的講述,我們每個(gè)人都仿佛置身第一現(xiàn)場(chǎng),成為這段忘年畸戀的“窺私者”。誠(chéng)然,從獵奇角度看,這段關(guān)系里也有最挑動(dòng)大眾神經(jīng)的忘年戀、女強(qiáng)男弱、情感控制,甚至是暴力,不過無論導(dǎo)演手法還是演員表演都極盡克制,這令這段情史變得幽微而深刻——90分鐘里一股難以名狀的悲傷與熱烈,隨緩慢移動(dòng)的長(zhǎng)鏡頭暗涌。

整部影片還有一個(gè)有意為之,那便是杜拉斯的“不在場(chǎng)”。要知道,采訪的發(fā)生地,正是她與揚(yáng)同居的郊野別墅。而采訪揚(yáng)的,也正是她的鄰居兼閨蜜米歇爾。足見這場(chǎng)訪談哪怕不是她的主張,也獲得了她的默許。但,整部影片只透過米歇爾的視角,隔著窗戶給到杜拉斯模糊身影。但事實(shí)上,杜拉斯又處處“在場(chǎng)”。揚(yáng)的每一句都關(guān)于她,采訪中不接不休的鈴聲,是杜拉斯的厲聲提醒。而在零星的補(bǔ)充歷史采訪和片場(chǎng)記錄里,處處可見她對(duì)揚(yáng)的絕對(duì)控制。她引揚(yáng)進(jìn)入自己的鏡頭,卻厲聲呵斥對(duì)方的不專業(yè),甚至不惜使用貶低的字眼。
比起電影,現(xiàn)實(shí)總是更加吊詭。從電影里看,這段在兩年后就似乎要分崩離析的關(guān)系,在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中竟延續(xù)了16年。其間,在揚(yáng)的協(xié)助整理下,杜拉斯出版了多部作品,最為人所熟知的,便是《情人》,它是少女杜拉斯的青澀愛戀回憶,而傾訴的對(duì)象,正是暮年時(shí)眼前的年輕情人,揚(yáng)。
由此來看,揚(yáng)的愛或許既不是米歇爾初步判定的“臣服”,也不是揚(yáng)自辯的“接納”。權(quán)力與控制從來都是流動(dòng)的,看似掌握絕對(duì)主動(dòng)與主導(dǎo)的杜拉斯,卻是最害怕?lián)P逃離的那個(gè)。于是,她用熱烈的愛,用暴君的話術(shù),用壓倒性的名望,用欲望的無休止索取,用幾近軟禁的控制,去留住這個(gè)年輕情人。而反過來,盡管揚(yáng)曾有過逃離,也用最直接的暴力來反抗著杜拉斯,可他終究癡迷于“擁有杜拉斯”這幾個(gè)字所代表的權(quán)力。
電影尾聲披露,揚(yáng)在將錄音交由米歇爾“暫時(shí)保管”后,直至2014年去世,都沒有要回。此后,米歇爾將錄音交由揚(yáng)的妹妹繼續(xù)保管。米歇爾逝世后一年,2016年在揚(yáng)妹妹的授權(quán)下,訪談才最終出版成書,書名就是《我想聊聊杜拉斯》,進(jìn)而有了這部影片。這不只是豐富了萬千喜愛杜拉斯讀者對(duì)于她的認(rèn)知,同樣的,也令諸多看客,從名人八卦軼聞猜測(cè)之中,回歸到更具普適意味的親密關(guān)系思考之中:愛是什么?愛可以帶來什么?愛又會(huì)摧毀什么?
可見,一段感情長(zhǎng)久的秘密,終究落在了文學(xué)之外,落在了電影之外。
題-2.png)